


追憶天國的母親--作者:漆新平
今天早上無意中翻閱到了2014年4月9日寫的《我愧對母親》,頓時淚如雨下,腦海里立刻浮現著無數母親身影。
母親離我而去已經一年了,我懷念母親,僅以這篇短文慰籍故去的母親,寄托兒子的哀思,愿天堂里的媽媽能夠感知到兒子錐心泣血般的哀傷和思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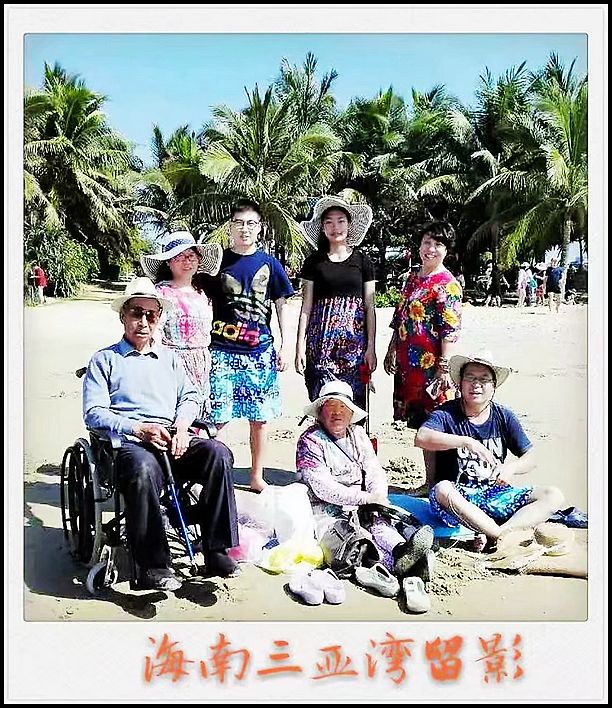
父母的相繼去世使我明白許多事情。那時間總覺自己很忙,在家吃頓飯就走,有時連飯都顧不上吃,說這事要辦,那位領導叫必須去。母親總愛埋怨的說“家里一頓飯不吃,就像掏火的一樣”(那時間人們都窮,就生火做飯都要到鄰居家炕洞里掏火,掏上就的趕緊跑)。有時間母親心疼而有不解的給親戚訴苦說“娃現在很忙,有時連飯都沒時間吃,在家住一晚上就更不行了”。看來父母親盼望我在家吃頓飯,和他們睡一晚上,嘮嘮家常都成了他們生活上的奢侈。難道真的很忙嗎?現在想起來真后悔。在家什么事都可以等,唯有孝敬父母這件事,真的不可以等。有時間提起電話想給父母打,忽然一想給誰打里。上有老,下有小,是我們每個成年人不得不面對的。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,必須努力地工作,努力地付出,努力地賺錢。

記得母親在世的時候,經常接到母親的電話 ,她在電話問我節假日放不放假、何時回家此類的問題,我一一作了回答,母親還會不厭其煩的說,她這段時間菜籽賣的很好,一天要賺幾十塊錢。聽著母親滿足的笑聲,電話這頭的我就像打翻五味瓶一樣難受。因為,在我這樣一個稍帶文人味的人看來,“母親”和“生意”兩個詞并提在一起,特別是疊加在一個上了年紀的母親身上,除了心酸心疼之外,更多的就是內疚了。
媽媽是從貧困年代走過來的人,無奈的生活環境讓他們那一代人都養成了自食其力,自力更生,艱苦奮斗,勤儉持家的性格和獨具的生活技能。從我記事起,就總看到母親幾乎每晚都在燈下做她的針線活。那時家家孩子都多,我家姐弟五個,做新的補舊的,針線活沒完沒了,母親向來是不服輸的人,總會讓我們姐弟幾個穿得利利落落,針線活自然就更多了。

我出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,在我5周歲的日子里,因醫療不發達二姐因緊急性痢疾命喪黃泉,我也生病高燒不退,眼看我呼吸困難,頻臨窒息,母親將我緊緊摟在懷里哀號不止。幸虧我的二舅舅見多識廣,從母親的懷里奪過我,背著我一路“急行軍”,跑到15公里以外的蓮峰公社尋求良醫診救,我才轉危為安。在此,我同樣要感謝以病逝的二舅舅。
持家除了勤勞,就是精打細算。一個家庭的吃飯穿衣,最能體現主婦的持家本事。在那個糧食短缺、物質匱乏的年代里,母親總是日夜忙碌,吃苦受累,挨凍受餓,讓我們兄妹四人吃飽穿暖。
到九十年代,我們的生活也好了起來,可母親開始學習“經商”了,那時她老人家已經近60歲了,雖然被歲月壓的直不起腰要來,但每逢集日,她依然要拉著滿滿當當的一架子車百貨,去離家3公里外的蒲河集市趕集。而且風雨無阻,執著的經營著她的“地攤生意”,編織著她心中的“商海之夢”。

那是1996年,當時我們家也并不富裕,只是因為有了外地工作的姐姐和被譽為“無冕之王”的我樹幟撐面,所以,當地村民總是把“富裕”跟我們家緊緊地連接在了一起。十幾年來,每當家庭財政發生嚴重“赤字”,生活出現困難時,母親總要說她那句永不更改的話:“我們也可以折騰折騰,賺些油鹽錢”。可我一直持反對態度,心想這樣大年齡,還干那體力活,咱家還沒困難到那個程度;再說讓同行,熟人以及地方官員看到時,我的臉往哪兒擱?可就在那一年秋季的一天,母親竟然背著我們“秘密”行動了,她用幾年省吃儉用省下來的一點積蓄購買了一些小商品,開始在距我家3公里的集市上擺攤設點,當起了生意人。我生氣地向母親下大了“最后通牒”,用責備而又懇求的口吻說:“你用多少錢,我哪怕少吃些、少用些給您,您再別給我去丟人現眼了!”哪知母親一言不發,只是用無聲來對抗我,依舊推著貨車,早出晚歸苦苦“經商”。她那“倔犟”的性格雖然叫我無可奈何,但我卻一直不樂意讓她這么做。每次在繁華的鬧市區看見頂烈日,冒酷暑,忙的不亦樂乎的母親,我總是既生氣又心疼,時不時地說些阻止她經商的話。直到第二年年底,弟弟要結婚,我擔心我支助的5000塊錢不夠辦宴席,正愁沒錢時,母親卻笑著用顫抖的雙手從裝滿小麥的木柜里面“挖出”一個用布頭縫制的包,里面是她一年多來靠擺攤設點賺來的錢,撥開層層“機關”細細一點,竟然有2000多元,這讓人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此時,母親瞇縫著雙眼一言不發的微笑著,可我們卻都沉默了起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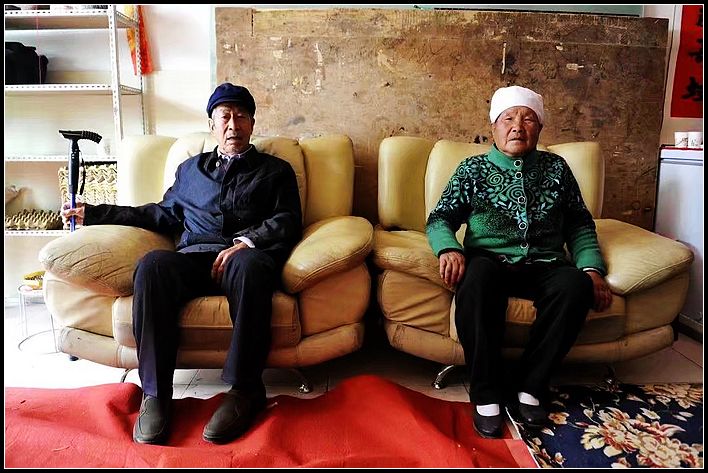
那時,母親雖然年老體弱,在市場的大潮中艱辛的搏擊,為全家的生活奔波著、張羅著。后來,每當回到老家,回到她老人家的身邊,她怕我阻止她繼續搞“經營”,總會壓著指頭“匯報”似的給我說:菜籽每包賺了多少錢,小商品長了多少錢,總共掙了多少錢。其實,我也很清楚,由于現在的生意不好做,一年下來僅僅才能賺七八百塊錢,說真的還不夠我們一頓飯錢呢,可母親總想著,雖然年紀大了但為家庭的付出一點是一點。那時間,每當望著母親那疲憊的面容,我總感覺到萬般心疼和慚愧,在為自己的虛榮心感到不安的同時,更為母親的偉大、樸實感到自豪。

現在回想起來,圍坐在父母親身邊,聽他們說說村里莊間趣事也成了美好的回憶,這是一種多么幸福的親情啊!如今我再也體驗不到那種幸福了,再也吃不到母親為我做的飯了。母親走的這天晚上,我出差在白銀,侄子媳婦打來電話說:“二叔,奶奶不說話了,估計快不行了”,遠在千里之外的我只能電話遙控他們找大夫,找村里懂事的老人”。那天晚上我徹底失眠,思緒飛到了2017年8月,蘭渝鐵路通車前夕,我很慎重的向父母承諾:“等蘭渝鐵路正式通車了,我帶你們兩體驗一下,順便到重慶吃火鍋,游玩一次”,父母顯得非常高興。但天有陰晴不定,人有旦夕禍福,離別總是讓人猝不及防,如今一個轉身就是陰陽兩隔。切記,不要讓你對父母的承諾,成為永無止境的等待,最后成為永遠的遺憾,致使你一直處于回憶和悲痛之中。

母親在世時,讀到有關母親的文章,似風兒滑過指尖一般,未有點滴觸動,為兒為母,兩種身份努力做好即可。母親走了,類同的文章從不敢輕易注目。對于“母親”這個世上最有溫度最具美好的詞藻,已成心中一個情結,不敢碰,一碰胸口就隱隱作痛,不能自已。塵世間沒有了母親,她已經去了天國。相信天國的母親,已化作天空的一顆星星,她給走夜路的兒子照亮前進的路,給所有走夜路的人照個前程。
母疼兒身,兒知母心。慈母的牽掛,是兒手中的碗,是兒身上的衣;慈母的牽掛,是兒居住的城市,是兒手中握的香煙,杯中的烈酒,是兒心中的喜樂與憂愁。
甘肅省廣電總臺電視新聞中心 漆新平
2021年4月9日

作者簡介:
漆新平,男,1972年6月出生,研究生學歷,現在甘肅省廣播電視總臺電視新聞中心工作。2016年本人榮獲中國科協、中組部、中宣部等九部委聯合頒發的“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實施工作先進個人”光榮稱號:甘肅省第九屆青聯委員:2018年被甘肅省委宣傳部和省記協授予“十佳記者”光榮稱號:甘肅省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九屆理事:榮獲2020年度全國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行業領軍人才稱號。采制的新聞評論《沉重的蘋果箱》在第二十七屆中國新聞獎(2017年度)評選中獲得電視評論三等獎:新聞評論《"變味"的精準扶貧貸款》榮獲2017年度中國廣播影視大獎電視新聞類一等獎(中宣部最高級別獎):新聞評論《伸向低保戶的黑手》、《"咬人"的收割機》、《莫名其妙的“不良貸款”》、《初中生小洲被誤抓以后》等106篇稿件分別獲中央、省政府,廣播影視一,二等獎。

 關于我們|媒體合作|廣告服務|版權聲明|聯系我們|網站地圖|友情鏈接
| 友鏈申請
關于我們|媒體合作|廣告服務|版權聲明|聯系我們|網站地圖|友情鏈接
| 友鏈申請
甘公網安備 62010002000486號
Copyright©2006-2019中國甘肅在線(甘肅地方門戶網). All Rights Reserved